
从南华山村的绣台,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;从12名绣娘的小作坊,到1879人参与的多民族产业集群;从“会拿筷子就会绣花”的彝家传统,到串联十余民族共同致富的“指尖经济”——丁兰英用三十余年的坚守,让楚雄彝绣走出深山,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注脚。2025年7月,“匠心营造·至善云滇”团队走进丁兰英工作室,采访了这位深耕彝绣事业三十余年的非遗创承人。
归乡筑梦|当乡愁织进民族团结的初心
“我不要花衣服,我只要妈妈。”女儿七岁时的这句话,成了丁兰英的人生转折点。1990年代,23岁的她和11个彝族姐妹为生计背井离乡,为了翻倍的月薪,三年春节没回过家。电话里女儿的询问“妈妈长什么样”,牵挂着丁兰英的心,也种下了“每个留守儿童的眼神都在呼唤妈妈回家”初心。

“彝家女儿一学家二学才三学刺绣”,八岁跟着外婆、母亲学绣技的记忆,让她决心用彝绣留住更多妈妈。2008年,她在南华县开起小作坊,把11个姐妹从工厂拉回来。最初,质疑声四起,但看着残疾姐妹因寄钱回家而家庭地位提升,看着绣娘们手中飞针走线,彝绣助力她们增收致富,实现人生价值,绣出精彩生活的时候,丁兰英更笃定:“非遗传承不是一个民族的事,是所有想靠双手创造生活的人共同的事业。”如今作坊里,彝族的火焰纹、白族的洱海蓝、傣族的孔雀翎在同一幅绣品上交织,就像各族绣娘围坐在一起,用不同的方言聊着相似的生活期盼。
破局前行|在困境中绣出各民族共富的希望
创业初期的艰辛,藏在80平米作坊的隔布后——布前是各族绣娘的绣架,布后是堆放着各式纹样素材的仓库。为了招绣娘,丁兰英曾挨家挨户敲开彝、白族亦或是汉族农户的门,用“你看这朵马缨花,和你们民族的图腾多像”拉近距离;培训时,她自掏腰包回收绣娘不熟悉技法的“废品”,笑着说:“多练几次,咱们就能把各民族的美都绣活。”

动人的是带动彭宗旺的故事。这位下肢瘫痪的彝族汉子,曾拖着纸板在烈日下谋生,丁兰英用“凑人数领补贴”的“谎言”拉他进班,又用“你的针脚最达标”的鼓励留住他。如今,彭宗旺不仅带出了傈僳族、纳西族的徒弟,更让男性绣工成为工坊里的“新风景”。“他们不是不行,是缺一个彼此扶持的机会。”

2014年,政府的小微企业补贴和10万元的创业贷款像“及时雨”一般出现了。如今彝绣成为了普惠的“民生工程”。丁兰英的彝绣也跨越了民族的界限,一方工坊,成为了民族团结、共同富裕的最好展示。
守正创新|让老手艺拥抱新潮流
“光传承不够,得让彝绣变现。”丁兰英发现,传统大红大绿的纹样难以留住年轻人。于是她和女儿分工:自己坚守传统技法,女儿则融入现代设计,将彝族火焰纹、马缨花提炼成文创元素,绣在卡套、背包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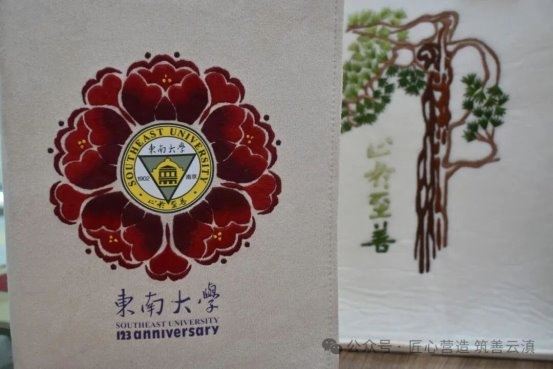
东南大学的帮扶更让彝绣“破圈”:东大设计团队将传统纹样与校园文化结合,南京的18个驿站、全国18个展点,让彝绣走进都市。如今,南华的绣娘平均年龄降至20-30岁,“00后”让刺绣走出传统的桎梏,让老手艺有了新流量。“纹样不变,颜色可变;传统不丢,时尚要追。”她带着团队与运动品牌合作,让彝绣元素出现在潮牌上;设计的“红石榴”绣品获全国乡村工匠金奖,党旗与石榴籽的意象,道出“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”的深意。这一根根彩线,正串起越来越多民族的文化共鸣。

绣娘蜕变|从指尖艺术到乡村振兴
在丁兰英看来,乡村振兴“不光是修公路、建房子,更要留住人”。如今,南华县“村村有绣娘”,车间开到乡镇里,各民族妇女们背着娃绣着花,既能照顾家庭,又能靠着刺绣补贴家用。曾经连村委都见不到的农村妇女,如今能与省委书记、大学校长交流,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不再是口号。
残疾绣娘从角落自卑到自信微笑,跨民族通婚在团队里成常态,彝绣成了无声的“团结纽带”。“长城”绣品里藏着她的创业哲学:“爬长城要丢包袱,做事业要专一。”她带绣娘申报“乡村工匠”“传承人”,让她们明白“手艺能改变命运”。
向光而行|让非遗走出大山看世界
“先借船出海,再造船远航。”丁兰英不避讳当下的“代加工”阶段,却早已规划好自主品牌的未来。全国多个驿站、海外展点的布局,让彝绣从“深闺”走向国际。她期待有一天,年轻人穿着彝绣潮牌逛街,明星们身着彝绣礼服走红毯,让绣娘们知道,她们的针脚能绣出世界。“到那时,绣娘们才知道,她们的针脚连起的,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。”

从8岁学绣的彝家女,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;从12人的小作坊,到近两千人参与的多民族产业——丁兰英用一针一线证明: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能让各民族心手相连的活态文化。正如她所说“彝绣是无声的语言,绣出了民族情,也绣出了好日子。”这双手,绣过嫁衣,绣过乡愁,而指尖的彩线,如今正绣着乡村振兴的蓝图,更绣着“中华民族一家亲,同心共筑中国梦”的明天。这门“无声的语言”,早已超越了针线的维度,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。(匠心营造·至善云滇团队 供稿)